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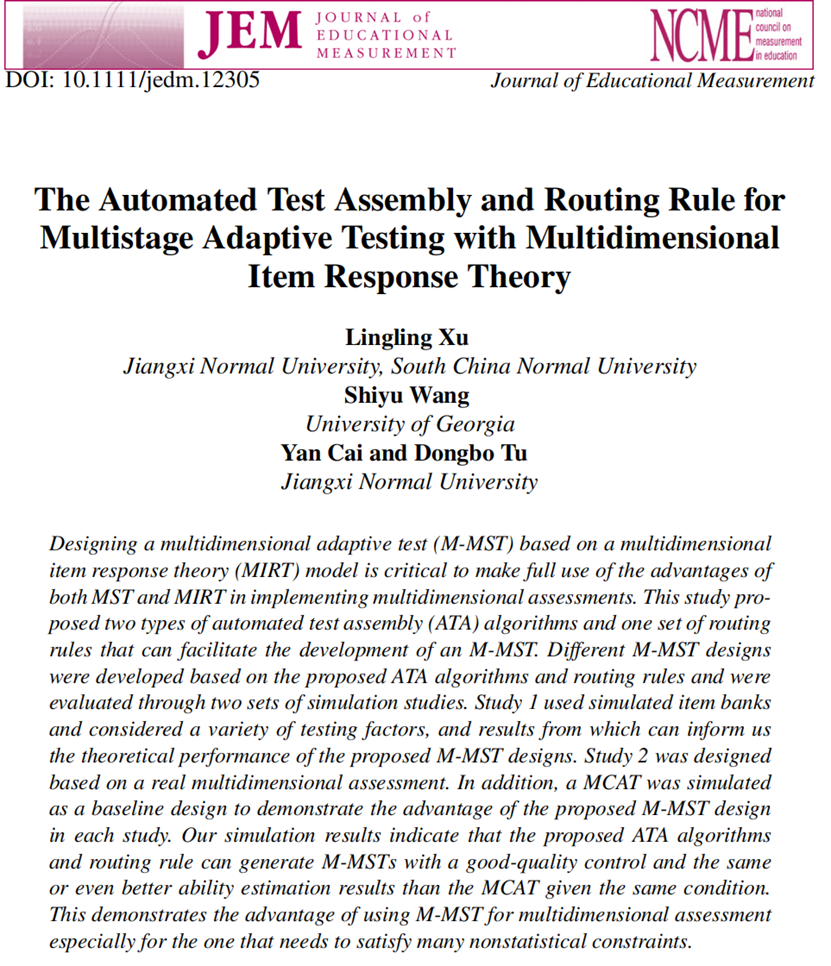
2022-05-06
多维计算机化多阶段自适应测验:自动组卷算法和路由规则背景介绍作者信息: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徐玲玲博士生 (第一作者),佐治亚大学教育心理系王诗宇副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蔡艳教授 (通讯作者)和涂冬波教授 (通讯作者)。原文出处:2022年1月发表于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SCIE/SSCI双收录)。文章具体信息:Xu, L., Wang, S., Cai, Y., & Tu, D. (2022). The Automatic Test Assembly and Routing Rule for Multistage Adaptive Testing with Mult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online. https://doi.org/10.1111/jedm.12305主要内容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现代测量理论的快速发展,心理和教育测验形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笔测验,正逐渐向计算机化测验过渡。在计算机化测验中,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CAT)和计算机化多阶段自适应测验 (multistage adaptive testing, MST)均属于自适应测验形式,它根据被试的作答反应为其选取下一步最合适难度的项目进行作答。两者的差异在于CAT属于项目水平的自适应测验,而MST属于模块水平的自适应测验。自适应测验的主要优势是“因人施测”和“量体裁衣”,即使用较少的、适合于被试的项目而达到对被试能力值更精确的估计。实证研究中发现:在相同的测验精度要求下,自适应测验的长度比传统的线性的纸笔测验的长度少50%到70% (Wainer et al., 2000)。近年来,MST相继成为多个大型考试项目的施测形式,如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医师执照考试、法学院入学考试和研究生入学考试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GRE)。可见,MST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青睐。在实际测验中,绝大多数心理与教育测验本质上都是多维测验。测验形式往往是由测量多个不同维度的能力的若干个测验共同完成。分析多维测验收集到的测验数据时,多维项目反应理论(mult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 MIRT)模型常被用于估计多维测量结构。根据多维评估的目的和性质,不同类型的MIRT模型被用于估计不同的多维测量结构(Gibbons & deGruy, 2019; Su & Huang, 2015)。而在自适应测验形式中评估多维测验,能够充分发挥MIRT和自适应测验的优势:不仅可以根据被试在测验中的表现同时估计被试多个维度的能力,还可以利用较短的时间达到更高的测量精度。因此,实现自适应测验在多维情境下的测验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且在心理与教育测量领域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前景。目前,已有不少文献对多维计算机自适应测验(multidimensional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MCAT)展开了研究。回顾相关研究发现,尽管MCAT在实施多维评估中具有实用性,但当测验需要同时考虑满足统计约束和非统计约束时,MCAT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MST因其在正式施测前使用自动组卷(automated test assembly, ATA)算法预先组建多个平行测验 (即平行面板),可以作为一种可尝试的解决方法。与MCAT的研究相比,MST在多维情境下 (multidimensional MST, M-MST)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目前,仅有Wang (2013)对其展开了调查,该研究假设多维测验中的每个项目仅测量能力向量的一个维度,并采用单维项目反应理论(un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 UIRT)模型进行测验评估。该研究中的M-MST设计本质上仍旧是多个单维MST设计的组合模式。尽管以该方式实施M-MST设计十分便利,但在实际心理与教育测验中,常常存在一个项目同时测量能力向量的多个维度的情况。因此,在M-MST设计中采用MIRT模型进行测验评估更适用于多维测量结构。综上,本研究旨在MIRT框架下提出多维MST(M-MST)设计。如前所述,M-MST设计需要预先组建多个平行面板,待平行面板构建后正式施测M-MST。其中,M-MST在预先组卷阶段依赖ATA算法;正式施测M-MST时,在自适应阶段基于路由规则将考生路由到下一阶段的最合适的模块。可见,ATA算法和路由规则这两大核心技术在M-MST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了适用于M-MST设计的两类ATA算法 (改进的标准化加权绝对离差启发[normalized weighted absolute deviation heuristic, NWADH]算法、改进的混合线性规划[mixed-integer programming, MIP]算法)和一类路由规则(改进的近似极大信息量[approximate maximum information, AMI]路由规则)。本研究通过模拟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评估所提出的M-MST的性能表现,还将与作为基线设计的MCAT进行对比,以明确M-MST的优势。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基于所提出的两类ATA算法和路由规则的组合均可以生成具有良好的测验组卷质量的M-MST设计。此外,相对于MCAT设计,M-MST设计还可以获得相同甚至更好的能力参数返真性结果 (结果见表1~4,图7~8)。上述结果也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结果见表4)。本研究在MIRT框架下执行M-MST设计,可以充分发挥MIRT和MST两者的优势。本研究为施测M-MST设计,提出了两大核心技术:ATA算法和路由规则。此外,为求解改进的MIP模型,还开发了随机分组MIP求解器。模拟与实证研究均表明,基于所提出的两类ATA算法和一类路由规则的组合均可以生成兼具良好测验组卷质量和能力参数返真性的M-MST设计。研究结论进一步说明,使用M-MST设计在评估需要满足非统计约束的测验形式时具有明显的优势性。本研究也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多维情境下实施MST设计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建议。主要参考文献:[1]Luecht, R. M. (1998). Computer-assisted test assembly using optimization heuristics.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2(3), 224–236.[2]Luo, X., & Kim, D. (2018). A top-down approach to designing the computerized adaptive multistage tes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55, 243–263.[3]Segall, D. O. (1996). Multidimensional adaptive testing. Psychometrika, 61(2), 331–354.[4]Wang, X. (2013). An investigation on computer-adaptive multistage testing panels for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稿件来源:教育统计与测量前沿

2018-09-04
面对全球经济与社会变革,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出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素养相关文件。基于此,为进一步探索在数学考试评价中如何有效渗透核心素养内容,选取PISA数学测试中的典型评价题目,分析数学考试评价对于核心素养的渗透情况。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考试评价应具备四个基本特征:基于现实生活情境;指向问题解决;体现开放性;反映数学本质。如何有效开发体现学生核心素养的测评题目,是未来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考试评价研究中的重要挑战之一。 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考试评价中测试题目的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基于现实生活情境。荷兰著名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HanFreudenthal)的“现实数学教育”思想,积极倡导数学必须连接现实,必须贴近孩子,必须与社会相关联,要体现人的价值,所以数学的学习,包括数学的考试评价需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PISA数学测试中的数学情境主要基于个人情境、职业情境、社会情境和科学情境,学生要将真实世界的信息转换至数学问题上,并建立正确的数学表征,再运用数学概念、步骤和方法解决数学问题,获得结论并做出恰当的解释,突出考查学生基于现实生活情境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基于情境性的问题,才更容易使学生发展其对数学的理解与认识,使数学的学习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第二,指向问题解决。问题解决是国际数学教育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口号,至今对数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问题解决是指发生在当时没有明确答案的未知情境里,是属于一种复杂、高层次的认知活动,学生需要将自己的已有经验或知识概念,进行各种方式的整合、协调,以产生个体满意的一连串的思维过程。 第三,体现开放性。《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要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正如PISA测试的题目,每道题目的解决策略都不是唯一的,为不同的学生在数学上得到不同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在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考试评价中,题目的开发应能体现开放性原则,使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数学现实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进而在数学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四,反映数学本质。数学的本质主要体现为数学基本能力和数学基本思想。张奠宙先生指出:“数学素质就是数学思维能力亦即数学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力,其核心则是逻辑思维能力。”史宁中教授指出:“数学基本思想是数学发展所依赖、所依靠的思想。”数学基本能力和数学基本思想是研究数学科学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学习数学,理解和掌握数学所应追求和达成的目标。因此,在数学考试评价中,测试题目的开发更应反映出数学的本质,发展学生的数学素养。 总之,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考试评价研究,除了要兼顾上述的基本特征外,更应重视如何有效开发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测评题目,尽管已有学者开展了该领域的研究,但其仍处于起步阶段,这应成为未来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考试评价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之一。 出处:周达,杜宵丰等.基于核心素养的数学考试评价研究:PISA典型题目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8(09):44-48.(有删减)

2018-07-29
跨学科核心素养具有情境性、整体性等特征,给跨学科核心素养测评带来挑战。国际上主要通过核心素养具体化、测评方式多元化和积极应用信息通讯技术来实现对跨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这些经验给我国未来的课程改革带来启示:谨慎推进核心素养的具体化;着力提升教师的评价素养;积极开展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测评研究。 基于核心素养的测评应当如何实施,正成为国际组织、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研究机构以及学者探讨的热点话题,也成为一线教师关注的焦点。实际上,与传统学科联系比较密切的母语交流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已积累起丰富的测评经验(如PISA、PIRLS和TIMMS测试),而跨学科核心素养测评却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为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部分国际组织和国家已成立专门的研究团队并进行了先期探索。考察这些国家跨学科核心素养测评的实施路径,将为我国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的实施带来有益启示。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即将拉开帷幕,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全方位、多层次测评体系。传统的纸笔测验在测查学生的部分核心素养方面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跨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方面则略显乏力。目前,关于跨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已引起国内部分学者和专家的研究兴趣,并开发出了一些外部评估的工具。有理由相信,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化和推进,跨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评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进一步具体化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构建更为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在外部评估方面,依靠来自不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力量,开发出高质量的测评工具,并不断修改、验证,使其趋于稳定、成熟;积极探索ICT在教育测评中的应用,努力使测评与学习二者互相融合。在学校层面,要着力培养和提升教师的评价素养,指导教师掌握表现型评价的一系列操作技术;鼓励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程进行评价,发展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只有多元化的测评方式被教师和学生群体理解、掌握并应用,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才会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未来教育正在迎来“e测评”时代,“嵌入式评价”范式将会受到更多重视。“嵌入式评价”具有的自动反馈、拟真环境、虚拟世界等特征能够更客观、精准地对学生的跨学科核心素养进行测评,同时还可以使测评与学习合二为一。我国基于计算机的测评起步较晚,相关技术不够成熟,在这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我们在继续沿用并不断改进、完善传统测评方式的同时,也要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力度。如前文所述,美、英等国在基础教育测评中积极探索基于计算机的测评应用已取得一定经验,这也是我国未来教育测评研究的重要方向。有理由相信,随着基于计算机测评技术的突破以及应用的进一步普及,必将给跨学科核心素养测评带来新的希望。 出处:黄志军,郑国民.国际视野下跨学科核心素养测评的经验及启示[J].教育科学研究,2018(07):42-47.(有删减)

2018-05-03
新手教师处于教师专业成长的起始阶段,这一阶段是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最具可塑性的阶段,也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内在关键期”,因而新手教师专业成长应受到充分重视。为深化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促进新手教师专业成长,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与分析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本研究运用元分析方法梳理21 世纪以来我国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现状,以期揭示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热点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为后续研究助益。 (一) 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趋向 1. 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作者背景多样化趋势明显 从学位论文的作者背景看,2001—2006 年,作者背景多是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2007—2010 年,作者背景出现了教育技术学和学科教学专业;2011—2016 年,作者背景还出现了教育史、高等教育、小学教育、学前教育、成人教育学和特殊教育学,另外还有体育教育训练学、汉语国际教育、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从期刊论文作者的背景看,作者除高校教师和研究生外还有教师进修学校和中小学继续教育中心的研究员、教务处和招生处行政人员以及一线小学教师和幼儿园园长等。由此可见,作者的背景越来越多样化。研究作者的多样化说明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受到更多专业背景的学者关注,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显得愈来愈重要。 2. 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 2001—2006 年的研究内容是分析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趋势与策略、国外入职培训的介绍和我国入职培训、师徒制的研究以及新手教师工作困扰的调查;2007—2010 年研究内容开始丰富,出现了澳大利亚入职培训的引介,以及新的发展策略——反思,并且在现状调查研究方面出现了新手教师发展需求、实践智慧和专业素养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2011—2016 年的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出现了对新西兰和日本入职培训的介绍,并且由传统的“师徒结对”研究转为“学习共同体”的探讨,出现促进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技术支持和课例研究。“实践智慧”研究更加细致化和深入,涉及“课堂管理”“师生互动”“教材处理”“教学反思”等方面。从研究内容的发展过程来看,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已由关注外部的教师培训和工作困扰逐渐聚焦于提升新手教师的教学技能和实践智慧,从关注新手教师这一群体转而慢慢关注新手教师个体的差异。 3. 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不断增多 一方面,学位论文在研究成果中占较大比重,而学位论文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所以实证研究在整个研究成果占很大部分比例。另一方面,研究内容决定研究方法,2001—2006 年的研究内容集中在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概述和工作困扰的现状以及国外入职培训的介绍,该时间段以实践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为主;2007—2010 年的研究内容逐渐丰富,表现为现状调查逐渐增多和国外入职培训引介研究增多,相应地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开始增长;2011—2016 年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着力通过调查新手教师的个人生活史和课堂教学现状来探讨其发展机制,因而实证研究比较多。另外,研究内容增加了国内外入职培训研究的比较,所以比较研究有所增长。 4. 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对象多样化 2001—2006 年研究的对象只是中小学英语新手教师;2007—2010 年出现了语文、数学、地理、科学等学科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2011—2016年,中小学研究的对象逐渐增多且出现了音乐和体育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出现了高校英语新手教师以及幼儿园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且幼儿园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增长趋势明显。从这一发展历程看,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对象逐渐多样化。 (二) 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可进空间 我国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虽然已经取得初步发展,但仍有需要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首先,缺乏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研究。缺乏理论研究的原因有研究者层次不高且分散,未形成核心作者群,缺乏对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除此以外,可能的原因还有,新手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一部分,关于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研究不进行另外讨论。 其次,更多地注重外部培训研究,关注内在专业素养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入职教育层面和新手教师入职适应的现状调查方面,当然也存在新手教师的实践智慧、专业素养以及利用反思和课例研究促进专业发展的研究,但数量不多。 再次,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对象存在学科的偏向,英语学科新手教师的研究偏多,其他学科新手教师研究相对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其一,大部分研究者是教育学出身,所学专业是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学、教育管理学等,没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较多;其二,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多为学科教学、外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虽属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的一部分,但是新手教师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新手教师处于职业适应阶段,在角色转换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现实矛盾和内心冲突,如,如何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在“规训”和“自主”之间如何切换等等。因此,针对新手教师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理论研究,缓解新手教师的认知矛盾、提升新手教师的实践智慧显然是必要的。有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两难空间”中建构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的路径,这为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提供了启示,这些“两难”对于新手教师来说不可避免且难以处理,所以后续研究可以借鉴此种研究方法建构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简言之,未来研究需更多关注新手教师个人专业素养的提升,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深入剖析新手教师的个人生活史,分析新手教师在专业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内心冲突,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理论体系解释新手教师的生存状态,并以“心理状态的改进”为抓手提升教学技能;除此之外,仍需关注各学科新手教师的成长,提出促进各学科新手教师专业成长的共同方法和特殊路径。 出处:何灿娟, 徐文彬. 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元分析[J]. 教育科学研究, 2018(3).(有删减)

2018-04-12
教师轮岗,作为一种改造薄弱学校或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举措,要达成其目的,参加轮岗的教师必须乐意轮岗以及在新岗位上积极奉献。为此,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建立激励机制:在生活保障与经济补偿上满足轮岗教师的生理需要,在程序规范与操作透明上满足其安全需要,在人事关系与归属认同上满足其社会或情感需要,在双向沟通与选择自由上满足其尊重需要,在专业发展与个人成长上满足其自我实现需要。 轮岗使教师从原本稳定的工作环境转换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无论是学校条件、人文环境还是工作状态、个人思想等都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各种需要也随之产生。前文所述,如果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仅仅以各种评优晋升的虚渺承诺和微薄的交通、生活补贴作为对教师的激励,显然忽略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层次性及可变性等特征,只有在认识教师需要的类型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才能根据他们的不同需要进行相应的有效激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一) 生理的需要——生活保障与经济补偿 轮岗过程中,即使有些地区采取“保留原校工资待遇”的做法,但变换工作学校,也必然给教师带来诸多生活上的不便,如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不便照顾家庭、工作学校条件艰苦等带来的交通费及生活费成本增加,显然给教师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由此,教师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衣食住行这样的生理需要,这必然需要从经济上进行补偿和满足。我国常以日本的教师流动制为参照对象,在经济补偿和激励方面,日本给偏远地区教职员的待遇已不是停留在与城镇教师“同工同酬”上,而是更加优 越。其在1954 年制定的《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1974 年第四次修订)中规定,市、町、村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协助在偏僻地区学校工作的教员及职员的住宅建造和其他生活福利,应采取必要措施”。在该法中,还专门设有“偏僻地区津贴”一项,规定“对指定的偏僻地区学校或与其相当的学校工作的教员与职员,发给偏僻地区津贴,每月津贴额在本人月工资和月抚养津贴总额的25%以内,当教职员因工作变动或随校搬迁到偏僻地任教时,从变动或搬迁之日起三年内,对其发给迁居补贴,月补贴额在本人月工资和月抚养津贴总额的4%以内。此外,还有其它各种形式的津贴,如寒冷地区津贴、单身赴任津贴等。” 经济的补偿和激励是最能满足教师生理需要的激励手段,只有这些需要得到了满足,使教师在生活上和经济上无“倒贴”“吃亏”的情况出现,才能让教师安心轮岗。对此,笔者建议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试行“大学区”管理,学区内同工同酬,并给予在贫困地区、薄弱学校任教的教师相应的补贴和物质上的支持,首先确保教师的交通津贴、食宿安排等生活条件都得到保障和有效的落实。在补偿方案上,也不必严格按照“实报实销”的方式进行,可尝试制订一个略高于教师实际开支的补偿标准,方能起到激励的作用。 (二) 安全的需要——程序规范与操作透明 安全的需要,是指保护自己免受身体和情感伤害的需要,它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在的安全的需要,另一类是对未来的安全的需要。即,一方面要求自己现在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保障;另一方面,就是希望未来生活能有所保障。 很多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轮岗的实施方案时并没有具体说明教师轮岗的具体选拔标准、轮岗期限、人事关系、工资待遇等问题,因而引起部分教师的职业安全感缺失。 现行的教育人事管理体制中,教师的人事关系归属于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而使用和调动则由学校主导。据此,学校有权对教师进行全面的管理,包括自主安排教师进行轮岗的管理权,如自主确认教师参与轮岗的先后、期限及其回原校的时间、相关待遇等等。 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的不完善、过程的不明晰、不透明,极易滋生不公平行为,使教师产生不安全感。有些教师很难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轮岗,曾有学者对某地区的教师轮岗情况进行过调查,发现在“规定的人数、职称结构、年龄结构都达到了当年的比例要求的‘假象’下,却隐藏着有的学校根本不考虑教师的实际情况,采用抓阄的方法选定交流教师,有的学校领导公报私仇,借此机会把平时不太‘听话’的教师交流出去”等行为。这些行为显然是对教师情感上的极大伤害,在不明不白或公报私仇的情况下被“流放”到另一所学校,不免使教师群体陷入一种人心惶惶的状态,不知会不会下一个就会是自己“被轮岗”。而且,轮岗后的发展怎样,转出去之后能否转回来,何时才能回来,人事关系如何变动等等问题都会直接削弱教师的职业安全感。 教师轮岗制度的操作程序缺乏透明度、公开性是导致轮岗教师职业安全感缺失的主要原因。以绍兴市越城区的教师流动“转会制”的实施意见为例,实施对象及范围仅仅表述为“越城区文化教育局直属中小学中的在编在岗教师”,在工作要求一项中则要求“程序到位,认真实施。学校引进名优教师要从学校的实际需要出发,转出、转入教师必须经由学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作出决定,严格按程序操作,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在这样空泛的笼统表述下,轮与不轮、轮向何处等问题就可能受到学校和校长的利益左右,甚至出现“潜规则”现象。 减少轮岗操作中的人为性、主观随意性,增强教师的职业安全感,必须要规范操作细则,对人员的选任标准作出明确的表述,使程序有据可依,并使其所涉及的教师全程参与,做到公平、公正、透明,消除教师的疑虑和诸多的不确定性。 (三) 社会或情感的需要——人事关系与归属认同 社交或情感的需要包括友谊、归属及接纳方面的需要。教育是一种影响人的职业,教师必须与其所在的环境、其接触的学生、同侪等建立起情感的联系,因此,教师有较强的社会或情感的需要。 我国教师轮岗制度中人事关系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走关系动”的刚性流动,另一种是“人事关系、工资福利归原校保留”的柔性流动。由此,很多教师会产生归属感的混乱。“我到底属于哪个学校呢?”也有些教师觉得只是轮岗,反正不会在新学校长期任教,因而处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 对于轮岗的年限,从相关政策来看,最短的为半年,最长的为三年以上,不管其最终期限是多长,对于刚来到新学校的教师而言,所面临的都是崭新而陌生的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教师难以迅速融入新的教师群体,甚至会产生孤立无援的隔离感。更为重要的是,教师与学生情感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慢慢融合,逐渐形成稳定的师生关系,才能了解学生,因材施教。但轮岗往往使教师产生一种短期心理,很难真正融入到薄弱学校的教学中。如果教师由始至终都抱“过客”的短期心态,必然难以对新学校产生归属感,亦难以与学生维持真正深入、深厚的师生情,对于教师自身的发展也没有促进作用。 要满足教师社会或情感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即要增强其归属感,要使其“既来之,则安之”。接收学校应有所作为,首先要为轮岗教师的到来作好充分的准备,如生活安置、工作安排等,要让教师感受到学校积极、欢迎的态度;同时也应派出本校资深教师帮助新来的教师更深入地了解学校,在生活上和教学上给予及时的帮助和指导。另一方面,针对轮岗教师来到层次不同、生源与原校差异较大的学校可能会出现“不适应”甚至不知如何调整教法的情况,学校应调配经验丰富的本校教师,在学生管理和教学方法上给予支持,减少轮岗教师的彷徨感。 另外,教育行政部门应在实施方案或意见中明确轮岗教师人事关系的处理办法,使教师的身份得到确认和保障,避免教师产生短期心理和缺乏归属感的现象。 (四) 尊重的需要——双向沟通与选择自由 尊重的需要分为内部需要和外部需要。内部需要包括自尊、自主和成就感;外部尊重因素包括地位、认可或者说受人尊重。 沈阳市早在2003 年就开始实施教师轮岗制,更成为很多地区借鉴的范例,但2006 年当地的一份调查却显示,被动交流的、相对自愿参加的以及积极参与流动的教师数量比例分别为35.01%、37.47%、27.52%。尽管大部分地区的轮岗实施意见和方案都具有较强的鼓励性质,但仍难以真正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很多教师被动甚至被迫进行轮岗。从教师的自主性和自愿性而言,执行轮岗管理的学校领导或政策制度并没有充分尊重教师的个人意愿,也没有给予合理的、必要的商议和选择余地。 在很多刚性的教师轮岗中,几乎所有的程序和操作都由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一手包揽,教师只是被动服从命令。而且往往由于制度不完善,细则不具体,导致有的学校采取“一刀切”的形式,全然不顾教师的实际情况,缺乏人文关怀和必要的程序规范。 本文所选取的七个轮岗方案中,仅有淄博市沂源县的方案在关于交流对象的规定中明确了不需要参加交流的情况:“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教师和校长可不参加校际交流;为保护学校办学特色、学校传统项目、特色课程的领衔教师经区教育局批准,可暂不参加交流;因病、孕等原因不能坚持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暂不纳入当年度交流对象”;在交流形式中不仅提出了“计划指导交流、明岗竞聘交流、校际协作交流、个人申请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方式,更明确“要坚持组织选拔与教师个人志愿相结合,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教师校际交流工作”的要求。 除了以规定的形式保障教师享有的自主和自愿权利,教育部门和学校也应该积极拓宽交流对象选、任的途径,作出更多民主化、公开化的有益尝试。如,可尝试仿照人才市场的做法,教育行政部门为符合交流条件的教师建立人才档案,同时整理、公示区域内每所学校对于交流教师的需求情况,然后定期由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师、学校的供需情况进行匹配、推荐,或直接进行大型的“轮岗人才供需见面会”。只有充分尊重教师的意愿,给予教师充足的选择空间,才能真正调动起教师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并为其自愿作出的选择负起应有的责任。 (五) 自我实现的需要——专业发展与个人成长 成长与发展,发挥自身潜能,实现理想的需要,这是一种追求个人能力极限的内驱力。教育是一种影响人、塑造人的精神工作,从事这个职业的教师对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尤为强烈与迫切。 根据流动的主导者不同,可将教师流动划分为自主流动和计划流动。从流动主体的流动意愿来看,可划分为主动流动与被动流动。自主流动往往是一种积极的主动流动,因为教师通常是以改善自身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或着眼于未来发展而进行的“逐利性流动”。相对而言,如刚性轮岗这样的计划流动一般情况下需要教师服从组织的调动和安排,且一部分教师更是“人往低处走”,从优质学校轮岗到薄弱学校去。对于这部分教师而言,自身的专业发展成为了他们顾虑的主要问题。 从理论上及政策期望而言,教师轮岗应该是有助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如教师在轮岗中可以接触到不同类型的学校文化、不同氛围的教师队伍、不同素质的学生,带给教师环境的新鲜感,增强其与其他教师的交流,提供实施不同教法的机会等等,从而逐渐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但是,我们亦应注意到当中潜在的问题。从教师个人发展的规律看,一名教师成为成熟型教师,要受到时间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制约,教师流动增加了新教师在成长中的不稳定因素。现行的教师轮岗期限最短的为半年,一般为一到三年,有的则为“六年轮一岗”或者“满两届必须轮”等,这意味着,教师可能一直处于频繁的流动中,或者一名教师好不容易适应并熟悉了一所学校的教育教学,刚要进入成熟与提升的阶段,就要考虑重新轮岗的问题。另 一方面,教师轮岗也意味着教师可能遇到与原校基础和素质相距甚远的学生类型,一些原本在优质生源“浸泡”下成长起来的教师反而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学生层次的改变,甚至无法开展有效的教学工作,更不用说自身的专业发展。再者,每次轮岗都首先需要一段过渡时间适应新环境,包括校园环境、生活环境、组织文化等,并要重新培养教师间的同侪关系、师生间的感情与教学默契等,其所占用的精力和时间势必对教师造成一定的影响。 相对于实现区域教育公平、拉近教育资源差距等“公共利益”,教师的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诉求肯定更具吸引力和驱动力,因为那才是个人最真切的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实施轮岗工作时,应让教师感到轮岗并非只是上级的安排,而要让他们意识到这也是为他们提供提升、发展机会的举措。因此,政策要做好思想的引导,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为教师的自我实现提供可操作的方案及可实现的机会。在制定实施方案前,应详细、深刻地考虑区域内轮岗教师的年龄结构、能力水平、学科分布等因素,做好调研工作,继而制定长远规划。学校层面,不仅要认清本校的现实情况,对轮岗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行评估,更要从具体教师的个人层面进行分析,了解教师的需求及职业规划,使教师的轮岗成为其职业发展的一部分,让教师在轮岗中真正得到锻炼和提升的机会,从而促进教师的自我实现。 出处:黄炜添. 基于需要层次理论的教师轮岗激励分析[J]. 教育科学研究, 2014(12):62-66.(有删减)